


上篇《中国乡村振兴的五个根本问题(上)》从“一老一小”的显性问题,和乡村经济主要矛盾解析。本篇从政治、文化与社会理论创新角度思考。

乡村政治“矛盾”思考
乡村政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在于广大农民对政治“不感兴趣”。
这个结论不稀奇,毕竟自古如此。史学家秦晖就将中国传统政治概述为“国权不下县,县下唯宗族,宗族皆自治,自治靠伦理,伦理造乡绅”,传统社会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参与政治的。
国家政权真正进入乡村,广大农民全面接触政治,始于建国后的土地改革,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,在于“农民取得土地,党取得农民”,在于通过“彻底推翻乡村旧秩序,使中国借以完成20世纪的历史任务:‘重组基层’,使上层和下层、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”。
此后,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“人民公社体制”,以及80年代确立的“村民委员会”自治制度,都是相应历史背景下组织三农的有效探索。
今天,市场经济下的村民自治面临两极分化。一种是,由于经济利益,或上面的扶持资金充足,乡村富人、强人踊跃参政,拉选票、宗亲好友票乃至贿选屡禁不止。一旦当选,除了执行上级政府任务,更倾向于代表自身或小团体利益,在行政+自治体系中,两头占好处,难以防范。
另一种更为典型。以我家乡小村为例,地方经济落后,国家补贴有限且直接到村组、农户,村里没有“油水”,大家对谁当干部没有兴趣。村民直选通常成为一个过场,往往是镇里定好方向、村里提前打好招呼,大家照着填选票就行。还有不识字的,“你填谁我就填谁,帮我打个勾就行”。“村民自治委员会”也就基本成为上级政府的延伸机构。

这条线是明线。还有一条线与乡村无直接关系,却更为根本,那便是——中央集权与地方政府公司化之间的矛盾。
中央集权与地方政府公司化,都是时代发展之必然。中央集权不必说,除春秋外,中国自古盛世基本都是中央集权时期,结合中国多元、内倾型文化特点,中央集权更是维护国家统一、稳定,社会存续、发展的重要保障。
地方政府公司化,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分税制改革下,财权上交中央,地方要发展,必须充分调动各地积极性。一方面,GDP、招商引资、发展速度成为地方政绩主要指标,另一方面,地方政府“公司”之间形成了充分竞争,彻底激发了地方政府的活力。可以说,没有地方政府之间的自由竞争,恐难有经济的飞速发展。
但也要看到,正是这两项制度的汇合,在客观上,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乡村的边缘化。
尽管历届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三农,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,随着对“乡镇企业是否挤占城市工业”争论的定调,即明确要求乡镇企业“两头在外”,让出国内原材料市场和产品市场,以及裁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等等,三农领域在决策中的影响力被削弱。
到地方政府,由于庞大的公共支出、经济发展和竞争需求,向经营要效绩成为必然。最能出绩效、最快有产出的地方在哪里?招商引资、贩卖自然资源、产业园、新城区、房地产……便成为必然。
基层乡镇政府更难。可卖的东西有限,权限又小,既无财权,又无执法权、处置权,还必须冲在三农工作第一线。现今法治社会,农民自我意识增强,特别是老年人无所忌惮,往往端起碗来吃肉,放下筷子骂娘。基层干部权轻责重,普遍两头受气,工作压力巨大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,囫囵吞枣、应付了事、形式主义等问题,在所难免。
对地方政府“公司”来说,农业产出慢,且上限明显,缺乏想象空间。加之取消农业税费,三农不但不赚钱,反而要不断投钱、补贴,不但加不了分,反而成为“拖累”。如此,只有责任没有利益,只有风险缺乏回报,必然导致“公司”管理者的疏远,这再正常不过。
若非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党性要求,如此发展,在一般国家,三农与基层政府恐怕已产生矛盾对立。
一方面,中央已经高度认识到这个问题,要求五级书记共管乡村,打通上下条线,并加强基层治理、党性教育,三农管理正在改善。
同时,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,中国乡村政治建设不过七十年历史,从土改到大集体到村民自治,已经历过三次重大改革,虽都无法尽善尽美,但在历史长河中,不过一瞬。我们才刚起步,而且始终在进步。
另一方面,中央集权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政治架构,中间存在一定的社会空隙、管理空白,需要进行制度完善,这也是重大课题。中央提出的生态经济、生态文明转型,谋于长远,方向明确,相匹配的行政管理改革,相信也在路上。
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,幸未偏航。

文化断裂才是危机所在
客观来说,若把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分个轻重缓急,乡村问题,目前并不紧急:
乡村一老一小,虽被遗忘,好在生存无忧。以“发展”眼光看来,市场优胜“劣”汰,牺牲也是难免;
乡村经济,虽难以突破,但自给还是有余。农村居民虽然收入较低,但要算上庭院、副业经济,如种菜养鸡、种点果树、挖个笋抓个鱼等隐性收入,差距并没有数据显示的大。加上没有房贷、自然环境较好,生活质量甚至优于不少城市居民;

乡村政治,虽有改良空间,但当前情势,除了建房、新生儿办户口,农民常年无需找政府,基层政府呢,既无需向农民征税派粮,也无需靠三农出政绩。大家互不打扰,相安无事,也是不错;
要说政通人和,风平浪静,也是可以。真正的危机,在于被广泛忽略的乡村文化断裂。
今天去到中国的许多乡村,所见,物质盈余之下,往往是精神的极度空虚。
留守乡下的中老年人,麻将、扑克是主要活动。家乡小村,不管春节还是平时,不管刮风还是下雨,吃完早饭、中饭,几个固定打牌点必然人满为患。三顿饭、两场牌,就是许多村民的生活日常。
大人们打牌,省得小孩吵闹,又不懂如何与孩子们交流,随手丢个手机。去到各家一看,孩子们或独自端着手机,或三五成群,不是王者就是吃鸡,不是抖音就是快手,成天头都不抬。当城里孩子被各种培训、养成自律习惯的时候,早早放飞的乡下孩子,恐将越飞越低。
这些还是显性,移动互联网文化正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率侵袭着乡村。许多平常我们听都没听过的“垃圾”APP、小程序,最大的市场,恐怕就是老年群体和广袤乡土。今年过年回家,我就发现我60岁的父亲除了打麻将就是抱着手机看小说,说是免费、能攒金币“提现”,最后钱没提几块,倒是往里冲了不少钱。瞄了一眼,多是“特种兵回家发现妻子被侮辱复仇恶霸”“农家娇妻桃花多”之类。
老人在看,小孩在“写”。譬如一些“写”小说的APP,只需要简单设置人物,取个名字,打一些关键词,然后在对话框“快点”,就能自动生成“对话体小说”,堪称AI智能写作“高科技”。
我11岁的小侄女、10岁的外甥女就热衷于此。小侄女取了个“人间美女XXX”的名字,课“余”“写”了三个月。我偷偷关注了一下,全是《国民校草爱上我》《温柔错付人》之类,点击量数百万,是我写几年乡村、财经观察和文学作品阅读量之和。我是要羡慕呢,还是该自叹不如?
现代市场经济往乡下倾销劣质工业品的时代逐渐过去,倾销劣质文化商品的时代已经到来。
如果说劣质商品还有其客观市场需求,防不胜防,那黄赌毒、迷信、变种宗教的侵入则必须高压防范。此类情况,笔者此前文章已有不少描述,也是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多少清楚一些的事实,此不赘述。它们造成的社会隐患,则是直接且违法的,必须严防死守。

诸如此类的现象后,反映出来的根本问题,是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在加速消失。文化失魂,又缺乏自律和外部约束,面对现代市场经济的降维打击,只能没有抵抗力、分辨力的被动接收。
有一个现象,至今许多人包括知识精英都不能理解。我之所见,今天的乡下,包括偏僻的西藏、新疆牧区,农民家里普遍还贴着毛泽东的画像、供着其铜像。按理说,集体大公社下,农业价值被超常提取,农民普遍穷苦,吃不饱饭是常事。现今生活富裕,吃穿不愁,为何还怀念那个时代?
大集体时代,农民个人虽被压制,但也前所未有地感受到集体的温暖。彼时,集体虽不富裕,除了吃饭问题,集体同步(虽然是初步)解决了农民的养老、子女教育、医疗等问题。虽不富裕,但有依靠,令人心安。
重要的还有文化教化。在传统被打倒后,集体承担起乡村教化工作,除了平常的政治、信仰教育,农闲时,县、乡都有戏团、放映、文化站,村里往往也有地方戏团、舞龙舞狮队、文艺宣传队等,农民的精神世界并不贫瘠,且具有极强的向心力。
这里并没有任何要倒退、回归的意思,这也是不现实的。当前的现实是,千百年来维持乡村运转的传统文明,诸如宗族、乡绅长老教化、乡规民约等传统文化,已经被暴力革命打倒或被意识形态消解,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教化又被放弃,一面是旧的已去。
另一面是新的不来。改革开放以来,出于财政压力及发展经济,国家对三农领域逐步退出,农村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。但在文化、精神文明领域,又实在退之过快。
如果说城市、现代工业文明的信仰是自由市场,那市场并不能成为乡土信仰。传统文化虽弱化,但依然维持乡村运转,而市场虽好,却始终难以有尊严地融入。
现代自由市场下,对广大农民来说,一个灵魂拷问逐渐浮出水面:活着的意义是什么?
传统社会,中国农民主要为前人和后人活着:光宗耀祖、培育后代,这辈子贡献出去,时间到了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走。他将欣慰地去见祖宗,他将活着子孙后代的记忆里。
今天呢?光宗耀祖不再重要,后代掌控不了,也没法培育。“育”多了,反而被否定甚至攻击,适得其反;
为自己?好像想象空间又有限,拼死拼活,也就这个样。而真要不管不顾前人、后人,也还会被戳脊梁骨;
为信仰?主义来过一段时间,又不知道去哪了。被市场经济教育过后,再去捡回来,好像也不是那么个意思;
为钱?好像也只有为钱了。管他钱怎么来,有钱就有地位,就能获得尊重,说话声音就大。但怎样才能有钱?又好像没什么机会……
算了,反正日子过得去,那就得过且过,那就听之任之,那就还是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那就发发牢骚、有机会就骂骂干部,那就信一信谁谁谁传过来的XX教……
如此,没有意义,无所依凭,无从信赖。旧的已去,新的不来。文化的断裂,才是乡村各种乱象的根源所在。而精神的空洞,也容易给黄赌毒、邪教、不良意识形态可乘之机。

| 父亲入伙的戏团,因亏本于前年解散
问题的问题,往往不是问题本身。市场经济下,就土地谈土地、就经济谈经济、就政治谈政治,都恐将有失偏颇,都难以系统解决三农问题。文化的振兴,人心的振兴,恐怕才是乡村振兴首要解决的问题。
从百年前的梁漱溟、晏阳初,到今天遍布大地的广大乡建者,以及以河南修武乡村美学教育、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等地方实践,都明了于此,也都不约而同地从文化教化、唤醒自觉、重建乡土内生力量的角度着力。虽缓慢,却是根本的、正确的,值得各级政府、企业和社会的重视与借鉴。

社会理论创新问题
百年前,梁漱溟著《乡村建设理论》,特意在书名旁加了个副标——又名:中国民族之前途。在他看来,乡村文化断裂,不过是中国社会文化失调的缩影,乡村建设,也不过是以乡村为切入口,以图民族之复兴。
于今而言,虽不至如此,但仍具参考意义——今日乡村问题,何尝不是社会问题在市场弱势主体身上之投影,今天乡村振兴,何尝不是民族复兴之新切口?
钱穆先生在《中国历史精神》中总结到,“任何一个社会,定要有大家共同尊崇的一些对象,这社会才能团结。这大家共同尊崇的对象,才是教育的最高精神所寄托,所凭依。”
今日中国乡村建设之成就,主要来自市场经济的反哺,但问题的根源,也在于市场经济的唯“物”主义,与百年唯“物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叠加、糅合。当唯“物”成为当今社会“大家共同尊崇的对象”。物质繁荣的同时,也将人与社会不断“物化”。
此时,乡村与农民,能“物化”的东西实在有限——只有有限的土地产出和自身劳动力,再退一步只有更为有限的“器官”。
换句话说,面向“物化”的社会价值取向,乡村能贡献的只有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。劳动力因其市场弱势地位,不管是经济还是心理,始终难以真正接受、融入城市市场。同时,国家体制,决定了城市无法获得其最感兴趣的乡村资产——土地,使得城市与现代市场对乡土始终打不起足够热情。
能卖的东西太少,又不值钱,自然要陷于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底端。在现代市场经济话语体系下,中国农民的处境,恐难有本质改变。

未来在哪里?更根本的出路,在于社会发展模式的创新。
放眼中国近现代史,总体来说是一个学习西方的历史,工业化、城市化、商品经济、科学、民主、法制、生活方式、世界观……今天,诸多领域陆续反超“老师”,独领风骚。
要问何所缺?相对物质、外在,恐怕更是内在:有一些松动,有一些失去了点什么、又一时难以找补的空洞。
这个“空洞”,曾是传统文明、革命精神、共产主义建设精神、“抓到老鼠就是好猫”的市场化精神……今天的中国,就像武侠小说中,一个好学上进、历经磨难的青年,终于学成各种武林绝学,成为一代大侠。各种场面游刃有余,但装的东西太多(且越来越多),又都不可能放弃,就得承受各种内力冲突——如不加以融贯、突破、开创新功法,恐将面临走火入魔、经脉寸断之困局。
好在,当今的世界大变局,为我们创造着机遇。
百余年前,当中国的寻路者将目光投向西方,许多西方寻路者就已认识到西方发展模式埋藏的巨大隐患——西方哲学的主客体、二分法、二元论,西方市场经济的无限分工、细化,必将导致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社会的分化、对立。西方模式可以靠物质、靠不断细分推动科学进步,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本身的问题。
他们将目光投向中国的“道”,中国的“天人合一”,乃至中国高效的自然循环农业、庞大却稳定的村社群体架构……“绿色GDP”概念提出者、世界生态文明学科泰斗小约翰·柯布就认为,中国可能是高速现代化过程中,唯一还保留着悠久且完整乡村文化的国家,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!
面向未来,我们只有从意识形态及自由市场唯“物”的禁锢中跳脱出来,以“中国所拥有的伟大智慧、深厚的文化、长远历史的可持续农业传统,以及理性化低消费观的悠久传统,为人类发展引领另一种模式——即利用其生态和政治伦理传统,作为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基础,替代当前‘经济增长’和‘消费主义’指标为基础的世界观,构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机制”……这既是对当下的批评,也是挑战,更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。
今天,碳经济、生态经济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轴,从马列毛邓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,正构建起新时代发展框架。以融贯传统与未来的生态文明为OS(底层操作系统),搭载并融合意识形态、市场经济、数字化时代(而非相反),才是民族复兴与崛起的星辰大海。

而传统文明去哪里找、生态经济向哪里寻求突破?
答案显而易见。




 dxhuang520
dxhuang520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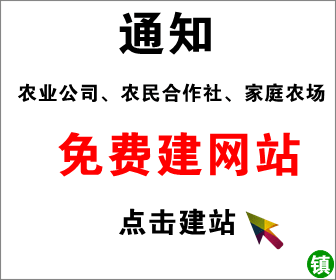
 苏ICP备18063654号-3
苏ICP备18063654号-3 苏公网安备 32011202000276号
苏公网安备 32011202000276号

